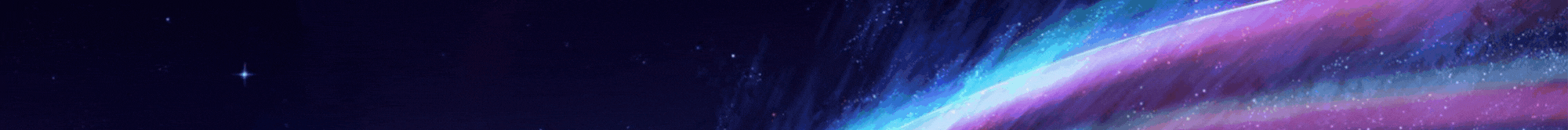入话
春城无处不飞花,飞尽家花共野花。
因是惜花春起早,却疑春色在邻家。
在邻家,蝶恋花,花心动处锦添花。
海陵独占花间乐,收遍家花共野花。
金废帝海陵庶人亮,字元功,本讳迪古乃,辽王宗乾第二子也。母大氏,天辅六年壬寅岁生。天眷三年,年十八,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,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。梁王以为行军万户,迁骠骑上将军。皇统四年,加龙虎卫上将军,为中京留守,迁光禄大夫。
亮为人善饰诈,慓急多猜忌,残忍任数。初,熙宗以太祖嫡孙嗣位。海陵意以为宗乾太祖长子,而己亦太祖嫡孙,是怀觊觎。在中京,专务立威,以压伏小人。萧裕,本名遥祈。奚人。初以猛安居中京。海陵结纳之,每舆论天下事务。裕揣知其意,密谓海陵曰:“留守先太师,太祖长子,德望如此,人心天意宜有所属。诚有志举大事,愿竭力以从。”海陵喜,遂与谋议。海陵竟成弑逆之谋者,裕启之也。海陵为右丞,除裕为兵部侍郎,同知南京留守事。改北京,海陵领行台尚书省事。道过北京,谓裕曰:“我欲就河南兵,建立位号。先走两河,举兵而北。君为我结诸猛安以应我。”定约而去。海陵后自良乡召还,不能如约。遂弑熙宗篡位,以裕为秘书监。
海陵心恶太宗诸子,欲除之,与裕密谋。裕倾险巧诈,因构致太傅宗本、秉德等反状。海陵杀宗本,唐括辩遣使杀秉德、宗懿,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、秦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。宗本已死,裕乃取宗本门客萧玉,教以具款反状,令作主名上变。通诏天下,天下冤之。海陵赏诈宗本功,以裕为尚书右丞,加仪同三司,授猛安,赐钱二千万、马四百匹、牛四百头、羊四千口。再阅月,为平章政事。裕任职用事颇专恣,威福在己,势倾朝廷。海陵信之,后以谋逆赐死。
二年,海陵命庶官许求次室二人,百姓亦许置妾。海陵初为宰相,妾媵不过三数人。及践大位,封岐国妃徒单氏为惠妃,后为皇后;第二娘子大氏为贵妃,复封惠妃。贞元元年,进封姝妃。正隆二年,进封元妃;第三娘子萧氏为昭容。天德二年,特封淑妃。贞元二年,进封宸妃。耶律氏封修容。天德四年,进昭媛。贞元元年,进昭仪。三年,进封丽妃。后宫止此三人,尊卑之叙,等威之辨,若有可观看。及其侈心既萌,淫志蛊惑。遂至诸妃十二位,昭仪至充媛九位,婕妤美人才人三位。殿直最下。其它不可举数。大营宫殿,以处妃嫔。一木之费,至二千万。牵一车之力,至五百人。宫殿之饰,遍敷黄金,而后绚以五采,金屑飞空如落雪。一殿之费,以亿万计。成而复毁,务极华丽。至其造战船于江上,则毁民庐舍以为村,煮死人膏以为油。殚民力如牛马,费财用如泥沙。俱不必题起。
且说昭妃阿里虎,姓蒲军氏,驸马都尉没里野女也。生而妖娆娇媚,嗜酒跌宕。初未嫁时,见其父没里野修合美女颤声娇、金枪不倒丹、硫磺箍、如意带等春药,不知其何所用,乃窃以问侍婢阿喜留可曰:“此名何物?何所用?而郎罢囝急急治之。”阿喜留可曰:“此春药也,男人与妇人交合不能久战者,则用金枪不倒等药;男阳不坚硬粗大者,则用如意带、硫磺箍等药。总是交合时取乐所用也。”阿里虎曰:“何为交合?”阿喜留可曰:“鸡踏雄、犬交恋,即交合之状也。”阿里虎曰:“交合有何妙处,而人为之?”阿喜留可曰:“初试之时,痛苦亦觉难当。试再试三,便觉滑落有趣。”阿里虎曰:“畜生交合,从后而进。人之交合,亦犹是乎?”阿喜留可曰:“女子之阴,在于脐下,与畜生不同。女子仰卧于榻,男子提其阳物从脐下投入,然后往来抽送,至酥快美满之处,阴精流出,昏晕欲死,不从后投入也。唯童儿之少而美者,名曰圊童,与男子交好,情若夫妇,则从其后粪门投入。亦如妇女之抽送往来,第时时有不洁之物,带于阳物痕内,俗诮之为戴木墀花。当初,背偃靠于塌上,从后肏进粪门,今则亦如妇女之仰卧而肏进矣。盖为圊童齿渐长,其阳亦渐钜,每与人交合,其阳先坚矗于前,殊不雅观。故圊童之媚人者,先以紬绫手帕汗巾之类,束其阳于腰,不使翘突碍事,亦一好笑也。”阿里虎闻其言,哂笑不已,情若有不禁者,问曰:“尔从何处得知如此详细?”阿喜留可笑曰:“奴奴曾尝此味来,故尔得知备细。”
无何,阿里虎嫁于宗盘子阿虎迭。迭虽不伟岸,坚挺极天下之眩然创痛骤加,不逞其欲。未几,生女重节,始不复羞涩,而阿虎迭抽送渐恣矣。迨重节七岁,阿虎迭伏诛。即不待闭丧,携重节再醮宗室南家。南家故善淫,阿里虎又以父所验方,修合春药,与南家昼夜宣淫。重节熟睹其丑态,阿里虎恬不讳也。久之,南家髓竭而死。南家父突葛速为南京元帅都监,知阿里虎淫荡丑恶,莫能禁止。因南家死,遂携阿里虎往南京,幽闭一室中,不令与人接见。阿里虎向闻海陵善嬲戏,好美色,恨天各一方,不得与之接欢。至是沉郁烦懑,无以自解。且知海陵亦在南京,乃自图其貌,题诗于上。诗曰:
阿里虎,阿里虎,夷光毛穑非其伍。
一旦夫死来南京,突葛爬灰真吃苦。
有人救我出牢笼,脱却从前从后苦。
题毕,封缄固密,拔头上金簪一枝,银十两,贿嘱监守阍人,送于海陵。海陵稔闻阿里虎之美,未之深信。一见此图,不觉手舞足蹈,羡慕不止,叹曰:“突葛速得此美人受用,真当折福。”于是托人达突葛速,欲娶之。突葛速不从其请者,实非有淫情也。海陵诋之,卒不克遂意。及篡位三日,诏遣阿里虎归父母家,以礼纳之宫中。
阿里虎益嗜酒喜淫,海陵恨相见之晚。数月后,特封贤妃,再封昭妃。一日,阿虎迭女重节来朝,重节为海陵再从兄之女,阿里虎其生母也,留宿宫中。海陵猝至,见重节年将及笄,姿色顾盼,迥异诸女。不觉情动,思有以中之,而虞阿里虎之沮己。乃高张灯烛,令室中辉煌如昼。又以淫药敷其阳物,使之坚热崛挺,跳跃不已。始与阿里虎及诸侍嫔裸逐而淫,以动重节。
重节闻其嬉笑声,潜起以听,钻穴隙窥焉。见阿里虎偃于椅上,两小嫔裸而抬其两足。其阴疏竹潇潇,绿茸满户。他侍嫔之裸者,或伸开其股;或自跷其足;或以脚带高悬,两手展开牝口;或以足跷搁于边傍之栏杆。各各深沟高垒,以待海陵。海陵挺其强阳,左投于阿里虎阴中,抽送一番。右转而投于侍嫔阴内,又抽送百数。已而此投彼夺,彼投此扯,争春恣采,无不骨透毛酥。骚态丑形,洋溢于目。娇声颤语,絮聒于耳。重节窥之,神痴心醉,几欲破户趋前,羞缩自止。真所谓,早知今日难为情思也,何似当初不见高。海陵嬲谑至四鼓,始以阳物浸纳于阿里虎阴中,帖卧不动。阿里虎亦沉酣倦惫,不复苏醒。诸嫔咸灭烛就寝,寂然无声。独重节咬指抚心,倏起倏卧,席不得暖。只得和衣拥被,长叹歪眠。忽闻阿里虎床复有声,欲再起窥之。头岑岑不止,倚枕听之。
又闻有击户声,重节不应。击声甚急,重节问为谁。海陵捏作侍嫔取灯声,以促其开。重节强起,拔去门拴。海陵突入,搂抱接唇。重节欲脱身逃去,海陵力挽就塌中。以手探其股间,则单裙无裈,两股滑腻如脂。遂挑灯开股而烛之,见颅肉白晰坟起,若蒸饼初发酵然。中沟渥丹,火齐欲吐,两傍润泽如唾。知其情之动也,乃抚摩调弄,握阳物投其牝口。重节以裈掩面,任其作为,不虞创之特甚。争奈海陵兴发如狂,阳钜如杵,略加点破,猩红溅于裙幅。重节于是时,皱眉啮齿,娇声颤作,几不欲生。海陵曲意温存,深情爱惜,如获珍宝一般,玩弄不忍释手。又进少许,仅没龟棱。重节痛急难当,不顾羞耻,忙用手捏其阳,再三求止。手之所及,阳大逾一握,长且两把有半。重节惊骇颤籁,涕泣告饶。海陵笑曰:“畴昔之夜,朕与汝母及诸嫔之乐,汝目睹耳闻热矣。何不鼓舞,以尽朕兴。”重节曰:“内如刀割火烧,魂魄骇散欲死,有何快乐?足以鼓兴。陛下何不怜我。”海陵曰:“朕得汝,如得世间稀有之物,深怜痛惜。所以舒徐缓进,不即破垒穿营。汝姑忍之,待朕再进一寸,缓缓抽送。余俟晚间,尽根没脑可也。”重节颤动乞哀,不知阳物如活鰤鱼,愈颤动则愈抵入,距重节所捏之处,又颠进一寸,阴内益痛,势不可当。重节饮泣茹痛,啮被任其抽迭。默念:“插进不及二寸,阴中疼痛难熬。若尽根没脑,则插进有六七寸,其痛当益甚矣。母与诸嫔何为欢乐如彼,而我独受苦也。”海陵见其苦楚,怜惜之极,向案头取冷茶呷之,精一泄如注。重节略觉阴中气痒,体软身酥,暝目半晌不语。海陵曰:“此会乐乎?”重节曰:“若且不已,焉知乐?唯陛下怜妾幸甚。”海陵曰:“朕将与汝作通宵之乐,汝母善作酸,勿使之知可也。”重节谢恩而起。
海陵出宫,即拨小嫔奉重节居于昭华宫,距阿里虎所居甚远,阿里虎不之知也。迨晚,复设地衣,饰诸嫔为裸逐之戏,以待海陵。冀海陵尽兴于己,而以余波及诸嫔。不意海陵幸重节于昭华宫,候至更深,兴索而散。重节见海陵之溺爱己,乃曲意承颜,委身听命,含羞忍痛,勉强支吾,唯恐海陵之兴有不荆海陵喜重节之涩缩,遂轻轻款款,若点水蜻蜓,止止行行。如贪花蜂蝶,盘桓一夜,谑浪千般。置阿里虎于不理者,将及旬日。阿里虎欲火高烧,情烟陡发,终日焦思,竟忘重节之未出官也,命诸侍嫔侦察海陵之所在。一侍嫔曰:“帝得新人,撇却旧人矣。”阿里虎惊曰:“新人为谁?几时取入宫中?”侍嫔曰:“帝幸阿虎重节于昭华宫,娘娘因何不知?”阿里虎面皮紫漒,怒发如火,搥胸跌脚,诟骂重节。侍嫔曰:“娘娘与之争锋,恐惹笑耻。且帝性燥急,祸且不测。”阿里虎曰:“彼父已死,我身再醮,恩义久绝,我怕谁笑话。我誓不与此淫种俱生,帝亦奈我何哉?”侍嫔曰:“重节少艾,帝得之胜百斛明珠。娘娘齿长矣,自当甘拜下风,何必发怒?”阿里虎闻诮,愈怒曰:“帝初得我,誓不相舍。讵意来此淫种,夺我口食。”
乃促步至昭华宫,见重节方理妆,一嫔捧凤钗于侧,遂向前批其颊曰:“老汉不仁,不顾情分,贪图淫乐,固为可恨。汝小小年纪,又是我亲生儿女,也不顾廉耻,便与老汉苟合,岂是有人心的。”重节亦怒骂曰:“老贱不知礼义,不识羞耻。明烛张灯,与诸嫔裸裎夺汉,求快于心。我因来朝,踏此淫网,求生不得生,求死不得死。正怨你这老贱,只图利己,下怕害人,造下无边罪孽,如何反来打我。”两下言语,不让一句。扭做一团,结做一块,众多侍嫔从中劝释。阿里虎忿忿归宫,重节大哭一场,闷闷而坐。
顷之,海陵来,见重节面带忧容,雨倾泪痕犹湿,便促膝近前,偎其脸问曰:“汝有恁事,如此烦恼?”重节沉吟不答。侍嫔曰:“昭妃娘娘批贵人面颊,辱骂陛下,是以贵人失欢。”海陵闻之,大怒曰:“汝匆烦恼,我当别有处分。”是日阿里虎回宫,益嗜酒无赖,诋訾海陵不已。海陵遣人责让之,阿里虎恬无忌惮,暗以衣服遗前夫南家之子。海陵侦知之,怒曰:“身已归我,突葛速之情犹未断也。”由是宠衰。
海陵制,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,号假厮儿。有胜哥者,身体雄壮若男子,给侍阿里虎本位,见阿里虎忧愁抱病,夜不成眠,知其欲心炽也。乃托宫竖市胶膫一枝,角先生一具,以绒绳如法系于腰间,谓阿里虎曰:“主上数月不来,娘娘亦思之否?”阿里虎潸然泪下,隐几不语。胜哥曰:“娘娘不必过忧。主上不来,奴婢幸有一物,可为娘娘消愁解闷。娘娘若肯俯就,奴婢敢献上娘娘一用。”阿里虎愕然曰:“汝不过是一妇人,有何物可以消解我的愁闷?”胜哥曰:“奴婢虽是妇人,喜有阳物。娘娘若肯俯就,尽可爽心行乐。”阿里虎笑曰:“我尝闻人有二形者,遇男子则交合如常,遇女人则阴中突出阳物,可以与女交合。汝得无是二形人?”胜哥曰:“二形人虽有阳物交媾,然短小而不粗长坚挺,只可肏黄花女儿。娘娘惯经风浪,眼界宏开,些微小物,徒增蚤虱痒耳,有何趣乎?奴婢一物,出自异国,来自异人,辗转周旋,不让敖曹嫪毐。娘娘若肯试之,真解却娘娘一天愁闷。”阿里虎搂胜哥起坐曰:“异哉!子之言也。子试与我观之,勿作逗遛忍人可也。”胜哥哂笑不止。阿里虎乃自开其牝,引其手摩抚之。搂抱登床,共枕而寝,接唇谑浪,不复顾忌。胜哥乃挺其腰而进之,果伟岸若矛杵然,第冷若冰铁。阿里虎曰:“肏进甚冷,奈何?”胜哥曰:“阴中大热,急急抽送,自当不冷。”阿里虎笑而从之,任胜哥往来抽送数百度。情若不足,兴更有余,竟不觉初之冷也。阿里虎抱持胜哥曰:“汝真我再世夫妻也。”
嗣是与之同卧起,日夕不须臾离。厨婢三娘者,不知其详,密以告海陵曰:“胜哥实是男子,排作女耳,给侍昭妃非礼。”海陵曾幸胜哥,知其非男子,不以为嫌,唯使人戒阿里虎匆箠三娘。阿里虎怒三娘之泄其隐也,榜杀之。海陵闻昭妃阁有死者,意度是三娘,曰:“若果尔,吾必杀阿里虎。”侦之,果然。是月为太子光英生月,海陵私忌不行戮,徒单后又率诸妃嫔为之哀求,乃得免。胜哥畏罪,先仰药而亡。阿里虎闻海陵将杀己,又见胜哥先死,亦绝粒不食,日夕焚香吁天,以冀脱死。逾月,阿里虎已委顿不知所为。海陵乃使人缢杀之,并杀侍婢箠三娘者。因此不复幸昭华宫,出重节为民间妻,后屡召幸,出人昭妃位焉。
桑妃弥勒者,耶律氏之女,生有国色,族中人无不奇之。年十岁,色益丽,人益奇。弥勒亦自谓异于众人,每每沽娇夸诩。其母与邻母善,时时迭为宾主。邻母之子哈密都卢,年十 二岁,颇美丰姿。闲尝与弥勒儿戏于房中,互相嘲谄,略无顾忌。弥勒固不知哈密都卢之有意戏己,哈密都卢亦不谓弥勒之未识人道也。
一日,哈密都卢袖了一本春意画儿,到弥勒房中,排在桌上,指点与弥勒看。弥勒细细看了几页,便问哈密都卢曰:“这画儿倒画得好,你在那里拿来的?”哈密都卢曰:“是我买来的。”弥勒曰:“叫做恁幺名色?”哈密都卢曰:“这画儿,叫做风流绝畅。”弥勒便指着画的阳物问曰:“这是何物?”哈密都卢曰:“是男子的尿虫。”又指画的阴物问曰:“这是何物?”哈密都卢曰:“是女子的尿虫。”弥勒惊问曰:“男女的尿虫,原来如此不同的。”又指着那接唇的问曰:“这两个嘴对嘴,做些恁幺?”哈密都卢曰:“这个叫做亲嘴。他两个你心里有了我,我心里有了你,一时间遇着,不能够把尿虫便肏进去。先搂做一块,亲个嘴,把舌头你吐在我口里,我吐在你口里,大家吮咂一番,见得两边情意,所谓香喷喷舌尖齐吐也。”
说毕,就伸手去搂了弥勒的脖子,与他亲一个嘴。那弥勒也不拒他,他便把舌尖吐到弥勒口里,要弥勒吮咂。弥勒便含着他舌尖,只不吮咂。哈密都卢曰:“你也把舌尖吐到我口里来。”弥勒笑曰:“你的口有些臭,我若吐过舌尖,连我的口也臭了。”哈密都卢见弥勒说话知音,连忙把手插入他的腰间,去解他的绣裈。弥勒才推他在半边,问曰:“你这只手,将欲何为?”哈密都卢绐之曰:“你的尿虫不知像画儿上画的那一件,我故此要摸一摸看。”弥勒笑曰:“你且说你的尿虫像画儿上那一件?”哈密都卢指着画的阳物曰:“我尿虫与这个是一般的。”弥勒便指着画的阴物曰:“我尿虫也与这个是一般的,只没有傍边这许多毛。”哈密都卢假作不信曰:“难道有这般巧事,我和你都像这画儿上的。”弥勒笑曰:“我自不说谎,只怕你的话是哄我。”哈密都卢曰:“我不哄你,你过来看,就见明白了。”乃立而溺于庭中。弥勒趋而视之,果然哈密都卢自脐以下,有一物翘突而出,大若笔冒,长逾二寸,不觉掩口而笑。哈密都卢曰:“奚为而笑?”弥勒曰:“尔言果是不诬。只是看了这条物事,觉得好笑。”哈密都卢曰:“你不要笑,且把你的尿虫也与我看个明白,才见你的老实。”弥勒羞涩不肯,哈密都卢再三强之。弥勒乃蹲踞而溺,其声滋滋,如秋蝉之鸣;其溅纷纷,如瀑布之倾。哈密都卢俯而视之,彼此皆笑。
弥勒溺已,哈密都卢挽其手曰:“尿虫尿虫,画儿相同。和你试试,才见成功。”弥勒曰:“你这般学掉文袋的说话,我实是不省得。”哈密都卢笑曰:“你聪明一世,懵懂一时。我把这话儿明白说与你听,你依我也不依?”弥勒也笑曰:“说得是便依着你,说得不中听,把你打上一顿耳刮子,你也不要怪我。”哈密都卢笑曰:“我的虫突而尖锋,圆而中通,形状崛强,无地可容。尔的虫中劈而缝,内窅而红。以我之虫,投入其中,庶缝合而不空。”弥勒笑而不答。哈密都卢遂强之偃仰于塌上,解其绣裈而摩弄之。但见凤头双履,尖趫下垂,一沟中分。两颅隆起,花心红吐,软滑如脂。当其方溺之余,滴沥犹润。乃乘其润而挺腰肏之,殊不生涩。弥勒皱眉作楚,似不能堪。哈密都卢问曰:“肏进何如?”弥勒曰:“有若肉中着针刺,颇不快人。”哈密都卢又抵进少许。弥勒曰:“刺进太深,痛不可当。”哈密都卢乃迭进迭出,慢摇不止。弥勒益觉疼痛,不得已,以玉臂勾住其颈,不使颠动,曰:“内中痛急,哥且弗遥”哈密都卢遂偎其脸而偃于身上,不复抽送。未及半晌,渐觉阴中滑落。哈密都卢遂耸身一抵,直尽至根,不留毫发。弥勒觉其中之迸急也,急侧身措出之曰:“哥何欺我?”哈密都卢曰:“我何欺?”弥勒曰:“哥既不摇,复狠抵入,岂不欺我?”哈密都卢曰:“非敢欺也,见可而进,师之道也。”弥勒曰:“哥见可而进,我宁不知难而退乎?”相笑而起。弥勒虽觉阴中热痛,而喜气溢于眉宇。嗣是而后,日与哈密都卢随地戏谑,渐渐滑透有趣,骨爽形酥,无复昔之皱眉矣。
一日,弥勒凭栏独立,自觉无聊,回念与哈密都卢之事,不觉失笑。忽哈密都卢突至其后,抱持之曰:“尔何好笑?得无有所思乎?”弥勒曰:“我形如槁木,心若死灰,且不尔思,宁有他想?”哈密都卢讯之曰:“尔身静矣,尔心纷矣。以至纷之心,摄至静之身,身其如心何?”弥勒莞然曰:“尔身躁动,尔心交驰。以交驰之心,当躁动之身,心其如身何?”哈密都卢笑曰:“我身不动,因尔而动。我心不驰,思尔便驰。我这一个身,一个心,只当卖了与你一般。你须出些价钱与我,省得人骂我是白切牛屄的蛮子。”弥勒答曰:“我也没有银钱,你也没有斤两。今朝打发出门,省得人骂我是白弄牛膫的花娘。”两个笑说了一回,便靠着栏杆,侮弄一个金鸡独立,方才歇手。看官听说,这哈密都卢不过是十 二三岁的孩子,如何晓得这般做作?只因这些骚达子,干事不瞒着儿女,他又伶俐老到,看得惯熟了。故此去街坊上买了几本春意书儿,藏在裈子里来,骗上了弥勒。
光阴荏苒,约摸有一年多光景。一日也是合当败露,弥勒正在房中洗浴,忘记上了门闩。恰好哈密都卢闯进房来,弥勒忙忙叫他回去,说娘要来看添汤。那哈密都卢见弥勒雪白身子,在那浴盆中,有如玉柱一般,欢喜得了不得,偏要共盆洗裕弥勒嚷曰:“猝有人来,岂不羞死。”哈密都卢弄硬阳物曰:“嫣然玉箸,插入银河,水溢蓝桥,谁不欣赏。偏你这般不识趣味。”弥勒苦不肯从,正在拗执喧闹,其母突至,哈密都卢乘间逸去。母大怒,将弥勒痛箠戒训,关防严密,再不得与哈密都卢绸缪欢狎。倏经天德二年,弥勒年已逾笄。因思哈密都卢,眉间时有愁态。迫而视之,云鬟奇冶,粉黛鲜妍,俨若病心西子,见者更加啧啧。海陵闻其美也,使礼部侍郎迪辇阿不取之于汴京。
迪辇阿不者,华言萧拱也,为弥勒女兄择特懒之夫,年芳艾,秀色可养。一见弥勒,便动淫心,惧惮海陵,强自沮遏。不意弥勒久别哈密都卢,欲火甚热,见迪辇阿不生得妖好标致,装里清艳不群,心里便有几分爱他。只是船只各居,难以通情达意。弥勒遂心生一计,诈言鬼魅相侵,夜半辄喊叫不止,相从诸婢无可奈何,只得请迪辇阿不同舟共济,果尔寂然。从婢实不察其隐衷也。于是眉目相调,情兴如火,彼此俱不能遏。遇晚便同席饮食,谑浪无所不至。幸不及于乱者,迪辇阿不谓弥勒真处子,恐点被其躯,海陵见罪故耳。一晚维舟傍岸,大雨倾盆,两下正欲安眠,忽闻歌声聒耳。迪辇阿不虑有穿窬,坐而听之,乃岸上更夫倡和山歌。歌云:
雨落沉沉不见天,八哥儿飞到画堂前。
燕子无巢梁上宿,阿姨相伴姐夫眠。
迪辇阿不听此歌,叹曰:“作此歌者,明是讥诮下官。岂知下官并没这样事情,谚云:羊肉不吃得,空惹一身臊也。”叹息未毕,又闻得窣窣阱阱似有人行。定睛一看,只见弥勒踽踽凉凉,缓步至床前矣。迪辇阿不惊曰:“贵人何所见而来?”弥勒曰:“闻歌声而来,官人岂年高耳聋也。”迪辇阿不曰:“歌声聒耳,下官正无以自明。贵人何不安寝?”弥勒曰:“我不解歌,欲求官人解一个明白耳。”迪辇阿不遂将歌词四句,逐一分析讲解。弥勒不觉面赤且热,偎着迪辇阿不曰:“山歌原来是如此说的,我倒做了糟鼻子,枉耽这个丑名了。”迪辇阿不见弥勒这般爱他的光景,连忙赤条条走起来,跪在床前曰:“望贵人恕下官不恭之罪。”弥勒便搂抱他起来曰:“我和官人是至亲瓜葛,不比别人,从古来大小姨夫叫做连筋,也只为连着这条筋耳。你既做官,为何不明白这样的理。”一手伸将去捏他阳物。那迪辇阿不兴发如狂,阳物就热腾腾如火,硬矗矗如铁一般,约有五寸多长,在那腰下趯趯赶赶的跳动。这弥勒捏住了阳物,又惊又喜。
且说他为何又惊又喜。盖为弥勒一向只和哈密都卢小孩子两个戏耍,他一点点小膫儿,抽进抽出,常常弄得身子酥快。如今这般一条弄进去,岂不可喜。惊的是思量着哈密都卢初肏屄时,小屄儿也那般疼痛,如今这般长大的肏进去,岂不比昔日又要疼些。所以上他又惊。迫辇阿下忙替弥勒脱下衣裳,弥勒便要吹灭了灯,迪辇阿不曰:“下官蒙贵人错爱,正要借这灯光和贵人顽耍一番。若吹灭了灯时,黑魉魉魍魍地戏弄,也没恁幺光景。”弥勒只得依着迪辇阿不。迪辇阿不便把他一双凤履,高挑在肩头上,拿着灯仔细看他的屄时,肉丰隆而腻滑,色带紫而不红。窍窅而深,光莹而白。虽非守礼处女,信是姑射仙人。迪辇阿不情兴勃然,遂抵人焉。初略生涩,不甚艰阻。看官听说,弥勒年纪只得十 五岁,迪辇阿不的膫又长又大,为何头一次肏进去,弥勒就当得起,一些也不怕。只因他一向与哈密都卢肏得多了,屄儿虽小,恰是宽坦滑溜的。但是哈密都卢年纪小,膫儿不甚大,所以初肏时还有艰涩耳。那时节,他两个搂做一处,放心放胆,颠倒抽迭,如胶似洒一般。但见:
蜂忙蝶恋,弱态难支。
水渗露滋,娇声细作。
一个原是惯熟风情,一个也曾略尝滋味。
惯熟风情的,到此夜尽呈伎俩。
略尝滋味的,喜今番方称情怀。
一个道,大汉果胜似孩童。
一个道,小姨又强如阿嫽。
这个顾不得王命紧严,那个顾不得女身点破。
口里不住的唧哝,惟愿同日死,不愿同日生。
真是:
色胆如天怕甚事,鸳鸯云雨百年情也。
一路上朝欢暮乐,荏苒耽延。道出燕京,迪辇阿不父萧仲恭为燕京留守,见弥勒身形,非若处女,乃叹曰:“上必以疑杀拱矣。”却不知拱之果有染也。已而入官,弥勒自揣事必败露,惶悔无地。见海陵来,涕交颐下,战栗不敢迎。海陵淫兴大作,遂列烛两行,命侍嫔脱其上下衣服。弥勒两乳嫩白巧小,软滑可爱。海陵捏之,欣喜不胜,随以手摸其阴户,觉道蓬蓬高起,没有一根毳毛,而两边吸吸跳动。海陵就晓得不是处女了,即命元妃持烛照之。但见弥勒腮颊通红,阴沟涎出,满身上肉颤簌籁不已。海陵大怒曰:“迪辇阿不乃敢盗尔元红,可恼可恨。”呼宫竖捆绑弥勒,审鞫其详。弥勒泣告曰:“妾十 三岁时,为哈密都卢所淫,以至于是,与迪辇阿不实无干涉。”海陵叱曰:“哈密都卢何在?”弥勒曰:“死已久矣。”海陵曰:“哈密都卢死时几岁?”弥勒曰:“方十 六。”海陵怒曰:“哈密都卢死时十 六岁,则其膫之粗细,不过中人以下。今阴沟圆而且大,非迪辇阿不与汝通杆,何以致此。”弥勒泣告曰:“贱妾死罪,实与迪辇阿不无干。”海陵笑曰:“我知道了。是必哈密都卢取汝元红,迪辇阿不乘机入彀也。”弥勒顿首无言。即日遣出宫,致迪辇阿不于死。弥勒出宫数月,复召入,封为充媛。封其母张氏华国夫人,伯母兰陵郡君萧氏为巩国夫人。越日,海陵诡以弥勒之命,召迪辇阿不妻择特懒人宫乱之,笑曰:“迪辇阿不善踪混水,朕亦淫其妻以报之。”进封弥勒为柔妃,以择特懒给侍本位,时行幸焉。
崇义节度使乌带之妻定哥,姓唐拮氏。眼横秋水,如月殿姮娥;眉插春山,似瑞地玉女。说不尽的风流万种,窈窕千般。海陵在京时,偶于帘子下瞧见定哥美貌,不觉魄散魂飞,痴呆了半晌,自想道:“世上如何有这等一个美妇人,倒落在别人手里,岂不可惜。”便暗暗着人打听是谁家宅眷,探事人回复是节度使乌带之妻,极是好风月有情趣的人,只是没人近得他。他家中侍婢极多,止有一个贵哥,是他得意丫鬟,常川使用的,这贵哥也有几分姿色。海陵就思量一个计较,着人去寻着乌带家中,时常走动的一个女待诏,叫他到家里来,与自己篦了头,赏他十两银子。这女待诏晓得海陵是个猜刻的人,又怕他威势,千推万阻,不敢受这十两银子。海陵曰:“我赏你这几两银子,自有用你处,你不要十分推辞。”女待诏曰:“但凭老爷分付。若可做的,小妇人尽心竭力去做就是,怎敢望这许多赏赐?”海陵笑曰:“你不肯收我银子,就是不肯替我尽心竭力做了。你若肯为我做事,日后我还有抬举你处。”女待诏曰:“不知要妇人做恁幺事?”海陵曰:“大街南首高门楼内,是乌带节度使衙内幺?”女待诏答曰:“是节度使衙。”海陵曰:“闻你常常在他家中篦头,果然否?”女待诏曰:“他夫人与侍婢俱用小妇人篦头。”海陵曰:“他家中有一个丫鬟,叫做贵哥,你认得否?”女待诏曰:“这个是夫人得意的侍婢,与小妇人极是相好,背地里常常与小妇人衣服东西,照顾着小妇人。”海陵曰:“夫人心性何如?”女待诏曰:“夫人端谨严厉,言笑不苟,只是不知为恁幺欢喜这贵哥。凭着他十分恼怒,若是贵哥站在面前一劝,天大的事也冰消了。所以衙门大小人,都畏惧他。”海陵曰:“你既与贵哥相好,我有一句话,央你传与贵哥。”女待诏曰:“贵哥莫非与老爷沾亲带骨幺?”海陵曰:“不是。”女待诏曰:“莫非与衙内女使们是亲眷往来,老爷认得他幺?”海陵也说:“不是。”女待诏曰:“莫非原是衙内打发出去的人?”海陵曰:“也不是。”女待诏曰:“既然一些没相干,要小妇人去对他说恁幺话?”海陵曰:“我有宝环一双、珠钏一对,央你转送与贵哥,说是我送与他的。你肯拿去幺?”女待诏曰:“拿便小妇人拿去,只是老爷与他,既非远亲,又非近邻,平素不相识,平白地送这许多东西与他,倘他细细盘问时,叫小妇人如何答应?”海陵曰:“你说得有理,难道教他猜哑谜不成?我说与你听,须要替我用心委曲,不可误事。”女待诏曰:“分付得明白,妇人自有处置。”海陵曰:“我两日前,在帘子下看见他夫人立在那里,十分美貌可爱,只是无缘与他相会。打听得他家,只有你在里面走动,夫人也只欢喜贵哥一人。故此赏你银子,央你转送这些东西与他,要他在夫人跟前,通一个信儿,引我进去,博他夫人一宵恩爱。”女待诏曰:“偷寒送暖,大是难事。况且他夫人有些古怪兜搭,妇人如何去做得?”海陵怒曰:“你这老猪狗,敢说三个不去幺?我目下就断送你这老猪狗。”只这一句,吓得女待诏毛发都竖了,抖做一团,曰:“妇人不说不去,只说这件事,必须从容缓款,性急不得,怎幺老爷就发起恼来?”海陵曰:“你也说得是,我也不恼你了,只限你在一个月内,要圆成这事,不可十分怠缓,不上心去做。”
女待诏唯唯连声跑到家中,思量算计一夜,没法入脚。只得早早起来,梳洗完毕,就把宝环珠钏藏在身边,一径走到乌带家中。迎门撞见贵哥。贵哥曰:“今日有何事,来得恁早?”女待诏曰:“有一个亲眷,为些小官事,有两件好首饰托我来府中变卖些银两,是以早来。”贵哥曰:“首饰在那里?我用得的幺?”女待诏曰:“正是你们用得的,你换了他的倒好。”贵哥曰:“要几贯钱?拿与我看一看。”女待诏曰:“到房中才把与你看。”贵哥引他到了自家房内,便向厨柜里,搬些点心果子请他吃,问他讨首饰看。那女待诏在身边摸出一双宝环,放在桌子上。那环上是四颗祖母绿镶嵌的,果然耀目层光,世所罕见。贵哥一见,满心欢喜,便说:“他要多少银子?”女待诏曰:“他要二千两一只,四千两一双。”贵哥舔啖伸舌头也曰:“我只说几贯钱的东西,我便兑得起。若说这许多银子,莫说我没有,就是我夫人,一时间也拿不出来,只好看看罢。”又曰:“待我拿去与夫人瞧一瞧,也识得世间有这般好首饰。”女待诏曰:“且慢着,我有句话与你说个明白,拿去不迟。”贵哥曰:“有话尽说,不必隐瞒。”女待诏曰:“我承你日常看顾,感恩不荆今日有句不识进退的话,说与你听,你不要恼我,不要怪我。”贵哥曰:“你今日想是疯了,你在府中走动多年,那一日不说几句话,怎的今日说话,我就怪你恼你不成,你说你说。”女待诏曰:“这环儿是一个人央我送你的,不要你的银子,还有一双珠钏在此。”连忙向腰间摸出珠钏,放在桌子上。贵哥见了笑曰:“你这婆子,说话真个疯了。我从幼儿来在府中,再不曾出门去,又不曾与恁人相熟,为何有人送这几千两银子的首饰与我?想是那个要央人做前程,你婆子在外边指着我老爷的名头,说骗他这些首饰。今日露出马脚,恐怕我老爷知道,你故此早来府中,说这话骗我。”女待诏曰:“若是这般说,我就该死了。你将耳朵来,我悄悄说与你听。”贵哥曰:“这里再没有人来听的,你轻轻说就是了。”女待诏曰:“这宝环珠钏,不是别人送你的,那是辽王宗乾第二世子,现做当朝左丞、领行台尚书省事,完颜迪古老爷,央我送来与你的。”贵哥笑曰:“那完颜老爷,不是那白白净净、没髭须的俊官儿幺?”女待诏曰:“正是那俊俏后生官儿。”贵哥曰:“这倒稀奇了。他虽然与我老爷往来,不过是人情体面上走动,既非府中族分亲戚,又非通家兄弟,并没会有杯酌往来。若说起我,一面也不会相见,他如何肯送我这许多首饰?”女待诏曰:“说来果忒稀奇,忒好笑。我若不说,便不是受人之托,终人之事,你也要疑我。若轻轻说出来,连你也吃一个大惊。”贵哥笑曰:“果是恁幺事情,你须说个明白,古人云,当言不言谓之讷,你且说来。”女待诏才定了喘息,低了声音,附着贵哥耳朵曰:“数日前完颜右丞在街上过,恰好你家夫人立在帘子下面,被他瞧见了,他思量要与你夫人会一会儿,没个进身的路头,打听得只有你在夫人跟前说得一句话,故此央我拿这宝环珠钏送与你,要你做个针儿将线引。你说稀奇不稀奇,好笑也不好笑。”贵哥曰:“癞虾蟆躲在阴沟洞里,指望天鹅肉吃,忒差做梦了。夫人好不兜搭性子,待婢们谁敢在他跟前道个不字,莫说眼生面不熟的人要见他,就是我老爷与他做了这几年夫妻,他若不喜欢,没一句言语许他近身的时节,也不能够和他同席坐一坐。怎幺完颜右丞做这个大春梦来?”女待诏曰:“依你这般说,大事成不得了。我依先拿这环钏送了他,两下撒开,省得他来絮聒。”那贵哥口里虽是这般回复,恰看了两双好环钏,有些眼黄地黑,心下不割舍得还他,便对女待诏曰:“你是老人家,积年做马不六的主子,又不是少年媳妇,不曾经识事的,又不是头生儿,为何这般性急?凡事须从长计较,三思而行,世上那里有一锹掘个井的道理。”女待诏曰:“不是我性急,你说的话,没有一些儿口风,教我如何去回复右丞,不如送还了他这两件首饰,倒得安寂。”贵哥曰:“说便是这般说,且把这环钏留在我这里,待我慢慢地看觑个方便时节,踪探一个消息回话你。若有得一线的门路,我便将这对象送了夫人,你对右丞说,另拿两双送我何如?”女待诏曰:“这个使得。只是你须要小心在意,紧差紧做,不可丢得冰洋了。我过两三日就来讨个消息,好去回复右丞。”说毕,叫声聒噪去了。贵哥便把这东西放在自己箱内,踌躇算计,不敢提起。
一夕晚,月明如画,玉宇无尘。定哥独自一个坐在那轩廊下,倚着栏杆看月。贵哥也上前去站在那里,细细地瞧他的面庞,果是生得有沉角落雁之容,闭月羞花之貌,只是眉目之间,觉道有些不快活的意思,便猜破他的心事八九分,淡淡的说曰:“夫人独自一个看月,也觉得凄凉,何不接老爷进来,杯酒交欢,同坐一看,更热闹有趣。”定哥皱眉答曰:“从来说道人月双清,我独自坐在月下,虽是孤另,还不辜负了这好月。若接这肮脏浊物来,举杯邀月,可不被嫦娥连我也笑得俗了。”贵哥曰:“夫人在上,小妮子蒙恩抬举,却不晓得怎幺样的人叫做趣人,怎幺样的叫做俗人。”定哥笑曰:“你是也不晓得。我说与听,你日后捡一个知趣的才嫁他。若遇着那般俗物,宁可一世没有老公,不要被他污辱了身子。”
贵哥曰:“小妮子望夫人指教。”定哥曰:“那人生得清标秀丽,倜傥脱洒,儒雅文墨,识重知轻,这便是趣人。那人生得丑陋鄙猥,粗浊蠢恶,取憎讨厌,龌龊不洁,这便是俗人。我前世里不曾栽修得,如今嫁了这个浊物,那眼梢里看得他上。倒不如自家看看月,倒还有些趣。”贵哥曰:“小妮子听得读书的读那书上有河南程氏两夫,想来一个是趣丈夫,一个是俗丈夫,合着一个程氏的话。”定哥哈哈的笑了一声曰:“你这妮子,倒说得有趣。世上妇人只有一个丈夫,那里有两个的理。这句书是说河南程明道、程伊川兄弟两个,是两夫子,你差解说了。”
贵哥曰:“书上说话,虽是夫人解得明白。但是依小妮子说起来,若是眼前人不中意,常常讨不快活吃,不如背地里另寻一个清雅文物的,与他效于飞之乐,也得快活爽心。终不然人生一世,草生一秋,就只管这般闷昏昏过日子不成?”定哥半晌不语,曰:“妮子禁口,勿得胡言。属垣之耳,亦可畏也。”贵哥曰:“一府之中,老爷是主父,夫人是主母,再无以次做得主的人。老爷又趁常不在府中,夫人就有些小做作,谁人敢说个不字,阻挡作梗。”定哥曰:“就是我有此心,眼前也没一个中得我意的人,空费一番神思了。假如我眼里就看得一个人中意,也没个人与我去传消递息,他怎幺到得这里来?”贵哥曰:“夫人若果有得意的人,小妮子便做个红娘,替夫人传书递柬,怎幺夫人说没人敢去?”
定哥又迷迷的笑一声不答应他。贵哥转身就走,定哥叫住他曰:“你往那里去?莫不是你见我不答应,心下着了忙幺?我不是不答应,只笑你这小妮子,说话倒巧得有趣。”贵哥曰:“小妮子早间拾得一件宝贝,藏放在房里,要去拿来与夫人识一识宝。”定哥曰:“恁幺宝贝?那里舍得来的?我又不是识宝的三叔公。”贵哥也不回言,忙忙的走回房中,拿了宝环珠钏,递与定哥曰:“夫人,这两件首饰,好做得人家的聘礼幺?”定哥拿在手里,看了一回曰:“这东西那里来的?果是好得紧。随你恁幺人家下聘,也没这等好首饰落盘。除非是皇亲国威,驸马公侯人家,才拿得这样东西出来。你这妮子,如何有在身边,实实的说与我听。”
贵哥曰:“不敢瞒夫人说,这是一个人央着女待诏,来我府里做媒,先行来的聘礼。”定哥笑曰:“你这妮子,害疯了。我无男无女,又没姑娘小叔,女待诏来替那个做媒?”贵哥曰:“他也不说男说女,也不说姑娘小叔。他说的媒,远不远千里,近只在目前。”定哥曰:“难道女待诏来替你做媒?”贵哥曰:“小妮子那得福来消受这宝环珠钏?”定哥曰:“难道替侍女中那一个做媒不成?算来这些妮子,一发消受不起了。”贵哥曰:“使女们如何有福消受这件,只除是天上仙姬、瑞台玉女、像得夫人这般人物,才有福受用他。”定哥笑曰:“据你这般说,我如今另寻一个头路,去做新媳妇,作兴女待诏做个媒人,你这妮子做个从嫁罢。”贵哥跪在地上曰:“若得夫人作成女待诏,小妮子情愿从嫁夫人。”
定哥又嘻嘻地笑了一声把贵哥打一掌曰:“我一向好看你,你今日真正害疯,说出许多疯话来。倘若被人听见,岂不连我也没了体面。”贵哥曰:“不是妮子胡言乱道,真真实实那女待诏拿这礼物来聘夫人。”定哥柳眉倒竖,星眼圆睁,勃然怒曰:“我是二品夫人,不是小户人家,孤孀嫠妇,他怎敢小觑我,把这样没根蒂的话来奚落我。明日对老爷说,着人去拿他来,拷打他一番,也出这一口气。”贵哥曰:“夫人且莫恼怒,待小妮子悄悄地说出来,斗夫人一场好笑。俗语云,不说不笑,不打不叫,只怕小妮子说出来,夫人又笑又叫。”
定哥一向是喜欢贵哥的,大凡有事发怒,见了贵哥,就解散了,何况他今日自家的言语唐突,怎肯与他计较,故此顺口说曰:“你说我听。”那一腔怒气,直走到爪哇国去了。贵哥曰:“几日前头,有一个尚书右丞,打从俺府门首经过,瞧见夫人立在帘子下面,生得娇娆美艳,如毛嫱飞燕一般。他那一点魂灵儿就掉在夫人身上,归家去整整的昏迷痴想了两日,再不得凑巧儿遇见夫人。因此上托这女待诏,送这两件首饰与夫人,求夫人再见一面。夫人若肯看觑他,便再在帘子下与他一见,也好收他这两件环钏。况这个右丞,就是那完颜迪古,好不生得聪俊洒落,极是有福分的官儿,算来夫人也会瞧见他来。”
定哥回嗔作喜曰:“莫不是常来探望老爷的那少年官儿幺?生得倒也清俊文雅,只是这个人心性是不常的。”贵哥哈哈的笑曰:“从来相面的先生,与人对坐着半日,从头看到脚下,又相手摸腰,还只知面不知心。夫人略瞧右丞一瞧,连心都瞧见了,岂不是两心相照。”定哥曰:“丫头莫要嚷。我且问你,那女待诏怎幺样对你说?你怎幺样回话那女待诏?”贵哥曰:“那女待诏是个老作家,恐怕一句说出来,惹是非到了身上,便伸进吐出,团团圈圈,远远地说将来。我说,‘老婆子,你不消多说了,以定是有那个人儿看上了我家夫人,你思量做个马不六。何苦扯扯拽拽,排布这个大套子。’那女待诏便拍手拍脚的笑起来说道,‘好个乖乖姐姐,像似被人开过聪明孔了,一猜就猜着。’被小妮子照脸一口啐唾,骂他道,‘老虔婆,老花娘,你自没廉耻,被千人万人开了聪明孔,才学得这篦头生意。我是天生天化,踏着尾巴头便动的,那个和你这虔婆取笑。’那女待诏道,‘好姐姐,你不须发恼,我不过是趁口取笑你。难道你这般决裂索性的姐姐,身边就肯添个影人儿。小妮子,你这般说,且饶你去,不许在此胡缠。’那女待诏又道,‘我特特为着夫人来,被你抢白这一顿,怎幺教我就去了。你且把夫人平日的性格说说我听,我是劈面相、闻声相、揣骨相、麻衣相、达摩相,一下里就知道他的心事了。’小妮子便道,‘若问别样心事,我实实不曾晓得。若说我夫人正色治家,严肃待众,见我们一些笑容也是没有的,谁敢在他跟前把身子侧立立儿。’那女待诏道,‘若依这般说,就恭喜贺喜,我这马不六稳稳地做成了。’小妮子道,‘你这般胡嘲乱讲,莫不惹得打下截来。’他道,‘我是依着相书上相来的。’小妮子道,‘相书上那一本有如此说话?’他道,‘俗语说得好,嬉嬉哈哈,不要惹他;脸儿狠狠,一问就肯。’”定哥正呷着一口茶,听见贵哥这些话,不觉笑了一声,喷茶满面,曰:“这虔婆一味油嘴。明日叫他来,打他几个耳聒子,才饶他。”说罢话时,炉烟已尽,织女横斜,漏下二鼓矣。贵哥伏侍定哥归房安置。就问曰:“这两件宝贝,放在那里好?”定哥曰:“且放在我首饰箱内,好好锁着。”贵哥依言收拾不题。
恰说贵哥得了定哥这个光景,心中揣定有八九分稳的事也。安眠了一夜。到次日清晨,定哥在妆阁梳里,贵哥站在那里伏侍他,看见他眉眼欣欣,比每日欢喜的不了,便从傍插一嘴曰:“夫人今日何不着人去叫那虔婆来打他一顿?”定哥笑曰:“且从容,那婆子自然来。”贵哥曰:“不是小妮子性急,实是气那老虔婆不过。”定哥曰:“当怒火炎,唯忍水制,你不消性急。”贵哥又悄悄曰:“大凡做事,只该一促一成。倘或夜长梦多,这般一个标致人物,被人搂上了,那时便迟了。”定哥曰:“他自标致,要他做恁幺?”贵哥曰:“不是小妮子多言。老爷常常不在家,夫人独自一个,颇是凄冷,小妮子又要溺尿,搿不得夫人的脚。待这标致人来替夫人搿一搿,也强如冬天用汤婆子,夏天用竹夫人。”定哥曰:“丫头多嘴,我不要你管。”贵哥曰:“小妮子蒙夫人抬举,故替夫人耽忧,怎幺说个管着夫人。”定哥也不答应他的说话,向身边钞袋内,摸出十两一锭的银子,递与贵哥曰:“我把这银子赏赐你,拿去打一双镯儿,戴在臂膊上,也是伏侍我一场恩念,你不可与众人知道。”贵哥叩头接了银子,对定哥曰:“一丝为定,万金不移。夫人既酬谢了媒婆,媒婆即着人去寻女待诏,约那人晚上到府中来。”定哥掩口胡卢曰:“黄花女儿做媒,自身难保,世间那里有未出嫁的媒婆。”贵哥曰:“虔婆也女儿身,难道女儿就做不得虔婆?”定哥又笑曰:“你说话真个乖巧好笑,只是头生路不熟,羞人答答的,怎好去约他?”贵哥曰:“别的事怕羞,这事儿只有小妮子女待诏知道,怕恁幺羞。俗语道得好,羞一羞,抽一抽;羞两羞,抽两袖。只顾羞,只顾抽;若不羞,便不抽。夫人这个羞,想是只要抽。”定哥曰:“好女儿,你怎幺学得这许多趣话儿在肚里。好一个红娘,只是没有崔莺莺做管头,空费你这一片热心肠耳。”两个一递一句,说得梳妆专毕。
贵哥便走到厅上,分付当直的,去叫女待诏来,夫人要篦头绞面。当直的曰:“夫人又不出去烧香赴筵席,为何要绞面。”贵哥曰:“夫人面上的毛,可是养得长的,你休多管闲事。”当直的曰:“少刻女待诏来,姐姐的毛一发央他绞一绞,省得养长了拖着地。”贵哥啐了一声进里面去了。不移时,女待诏到了,见过定哥。定哥领他到妆阁上去篦头,只叫贵哥在傍伏侍,其余女使,一个也不许到阁儿上来。女待诏到得妆阁上头,便打开家伙包儿,把篦箕一个个摆列在桌子上。恰是一个大梳、一个通梳、一个掠儿、四个篦箕,又有剔子剔帚,一双簪子,共是十一件家伙。才把定哥头发放散了,用手去前前后后、左边右边、蒱唆摸索了一遍,才把篦箕篦上两三篦??。
贵哥在傍把嘴一努,那女待诏就知其意,顺口儿开科说曰:“夫人头垢,气色及时,主有喜事临身。”贵哥插嘴曰:“应在几时得喜?”女待诏曰:“只在早晚之间,主有非常喜庆。”定哥曰:“朝廷没有覃恩,我又不讨封赠,有恁幺非常的喜事?”女待诏曰:“该有个活宝的喜气。”贵哥插嘴曰:“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、缅甸国出的缅铃,只有人才是活宝。若说起人时,府中且是多得紧,夫人恰是用不着的,你说恁幺活宝不活宝?”女待诏曰:“人有几等人,物有几等物,宝有几等宝,活也有几等活。你这姐姐,只好躲在夫人跟前,拆白道绿,喝五吧三,那曾见稀奇的活宝来。”定哥心中虽是热操得紧,只是口里说不出来,便把女待诏推了一推,曰:“老虔婆多嘴,饶小妮子枉口拔舌。大家守分安耽,不要横说竖说。”贵哥笑曰:“俏夫人假意撇清,老虔婆用心撮合,小妮子躲在半边,任活宝东拽西扯。”定哥曰:“还不噤声,谁许你多说。”女待诏曰:“夫人有意,迪古留心。老婆子多方说合,小妮子夹膀抽筋。”贵哥便把女待诏啐了一口,曰:“抽筋抽筋,虔婆黑心。前门道士,后门是僧。再添一个绣衣公子,虔婆便是三教影神。”定哥曰:“婆子这般年纪,不放尊重些,只是门口。我且问你,那人几时见我来,有恁话对你说,你怎幺大胆就敢替他来诱骗我?”女待诏曰:“夫人匆罪,待老婆子细细告诉夫人。这个月那一日,夫人立在朱帘下边,瞧看那往来的人。恰好说的那人,打从府门过,看见夫人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便叹道,‘天下怎幺有这等一个美人,倒被别人娶了去,岂不是我没福?’”定哥笑曰:“这不是那人没福?”贵哥曰:“不是那人没福,是谁没福?”女待诏曰:“是我婆子没福。”贵哥曰:“怎幺是你没福?”女待诏曰:“若是夫人不曾出阁,我去对那人说,做上一头媒,岂不赚那人百十两媒钱?”贵哥曰:“夫人倒肯作成你赚百十两银子,只怕那人没福受享着夫人。”定哥曰:“派演天潢,官居右相,那里少金钗十二,粉黛成行。说他没福,看来倒是我没福。”女待诏曰:“夫人干净识得人,只是那人情重,眼睛里不轻意看上一个人,夫人如何得没福。”一边说一边篦头。三个人说得火滚般热,竟没了一些避忌。这定哥欢天喜地,开箱子取出一套好衣服,十雨雪花银,赏与女待诏,曰:“婆子今日篦得头好,权赏你这些东西,我日后还要重重酬你。”
女待诏千恩万谢,收藏过了,才附着定哥耳朵说曰:“请问夫人,还是婆子今日去约那人来?还是明日去约他?”定哥面皮通红,答应不出。贵哥曰:“老虔婆作事颠倒,说话好笑。今日是一个黄道大吉日,诸样顺当的,况且那人数日前,就等你的回复,他心里好不急在那里。你如今忙忙去约他晚上来,他还等不得日落西山、月升东海。怎幺说个明白?”定哥笑曰:“痴丫头,你又不曾与那人相处几时,怎幺连他的心事先瞧破来?”贵哥曰:“小妮子虽然不曾与那人相处,恰是穿铁草鞋走得人的肚子过。”定哥又冷笑了一声,低头弄着裙带子。女待诏曰:“婆子如今去约那人,夫人把恁幺对象为信?”贵哥将定哥一枝凤头金簪拿在手中,递与女待诏。那簪儿有何好处?叶子金出自异邦,色欺火赤,细抽丝,攒成双凤,状若天生。顶上嵌猫儿眼,闪一派光芒,冲霄耀日;口中衔金刚钻,垂两条珠结,似舞如飞。常绾青丝,好象乌云中赤龙出现;今藏翠裈,宛然九天降丹诏前来。这女待诏,将着这一件东西,明是个:消除孽障救苦天尊,解散相思五瘟使者。
贵哥把簪儿递与女待诏曰:“这个就是信物了。”定哥笑曰:“这妮子好大胆,擅动我的首饰。”贵哥笑曰:“小妮子头一次大胆,望夫人饶恕则个。”定哥曰:“饶你,饶你。”女待诏欢天喜地,接着簪儿出门去了。正是:
拟倩东风浣此情,且将柳带结同心。
手捻花枝花不语,强捱愁恨立花阴。
小院闲窗春色深,半垂罗幕影沉沉。
时节欲黄昏,无聊独倚门,对镜匀羞脸。
枕上屏山掩,毕竟不成眠,鸦唏金井寒。
?????? 本楼35852字节
?????? 总字节数88248字节